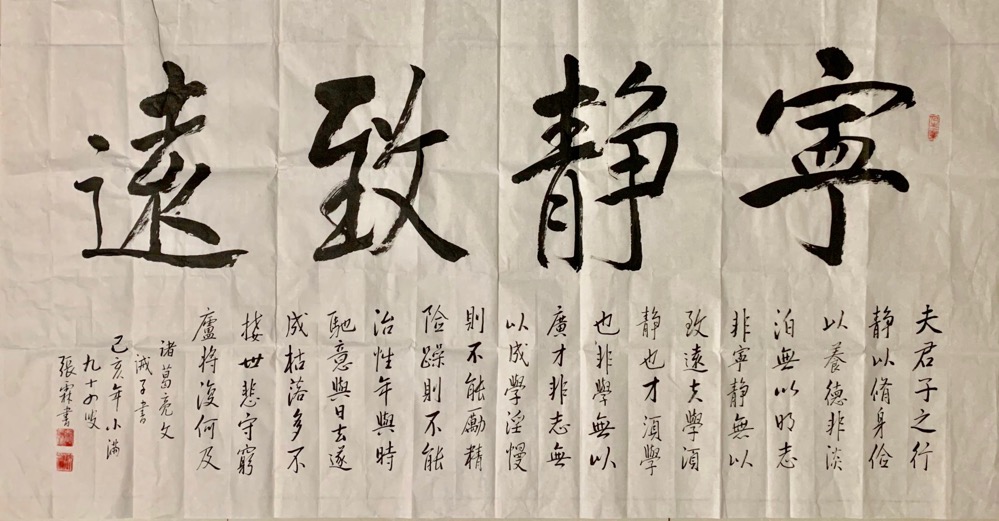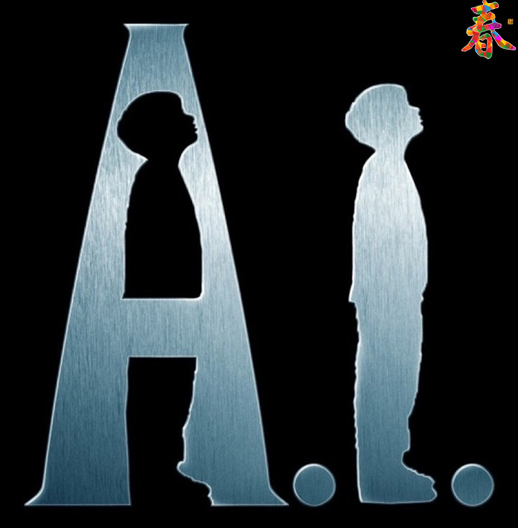文明与野蛮,从来都是一个问题。
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新几内亚时,被一个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朋友耶利问倒:“为什么你们白人制造了那么多的货物并把它运送到新几内亚来,而我们黑人却几乎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货物呢?”
戴蒙德教授当场语塞,二十多年后,他写出《枪炮、病菌与钢铁》作为回答。
在本书中,他通过对最近13,000年来关于人类的近代史的全景考察,试图从地理学、生物学、病菌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角度解读“人类社会的命运”的起伏。
他认为答案存在于公元前11,000年冰河期结束的年代,地理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各个大洲发展的不同。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路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环境尤其是地理环境的差异。
他甚至认为,如果一万年前,澳洲土著和现代欧洲人的祖先互换位置,那么现在澳洲土著可能不但占领了欧亚大陆,而且也占领了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而现在的欧洲人可能已沦为澳大利亚一些遭受蹂躏的零星分布的人口。
冰河时代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族群都过着四处漂荡、朝不保夕的狩采生活,而地理禀赋的不同让各地的农业发展有所不同。
气候适宜,物种繁多,作物茂密的地区,农业较为发达,大部分人能够过着定居生活,人群之间的交流沟通机会加大;农业生产带来的丰盛粮食则让某些人脱离生产劳动而从事技术创新,因此农业奠定了组织、文字、政治以及技术等等文明基石。
由此来看,欧洲文明的霸权建构的三大优势:钢铁,病菌,枪炮,无不与农业息息相关。在欧洲人的征服史上,枪炮与钢铁的作用众所周知,但戴蒙德对病菌作用的论述则令人耳目一新。
最为明显的例证在十六世纪,在墨西哥,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的交锋中,使白人取得决定胜利的不是传说的先进枪火对土著的屠杀,而是天花病毒。1618年,墨西哥大陆的2000万人因传染病减少到160万,95%的原住民便是死于白人带来的天花和麻疹。
科学表示,传染病菌多从动物身上变异而来,先传染给人,然后才在人类群体中传播。欧洲农业历史悠久,家畜众多,欧洲人几千年来与病菌频繁接触,已形成适应性;而印第安人则不然,农业的欠发达让他们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触的经验,肌体很少遭遇此类病菌,所以在天花面前溃不成军。
可见,病菌的优势也间接来自于农业。
戴蒙德认为四点因素决定了各大文明的竞争优劣:首先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其次是大陆之内传播和迁移的速度,第三点则是各大陆之间传播和迁移的速度,最后则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
因为欧亚大陆在这四个方面明显高于其他大陆,所以农业最为发达,这也为欧洲人扫荡世界铺平了道路——但是为什么不是亚洲人特别是中国人呢?
从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观点来说,中国的落后是令人诧异的。中国农业产生早,而且从华南到华北不同的作物物种都有分布,加上广阔的幅员和众多的人口,中国在农业诞生一万年之后还能进行高产的集约农业。
但地理的统一在政治上表现为经常性的稳定,进而带来内部的集权以及对外在世界的漠视。最具体的例证就是郑和下西洋在皇帝的一声令下就被停止,而哥伦布则可以找到不同的国王来支持他的冒险。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帝王一个偶然而不可逆转的决定,就让本来在航海处于上风的中国走向后退与封闭。
从某种象征角度来说,枪炮可以看作技术,钢铁则代表着资源,病菌则可以视为传播的隐喻。有了资源,必须利用技术才可使用,而有了前两者之后若无传播,任何优势都可以走向停滞甚至反面。文明如水,流水不腐是自然之理,保守不变是文明难解之痒,没有传播带来外来的交流对话甚至冲突,任何文明都会走向消亡崩溃。
戴蒙德的宏大论述体系暗合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的玩笑话:“文明,不过是一件百衲衣。埃及、巴比伦、希腊、罗马、印度、阿拉伯,什么地方的布条子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