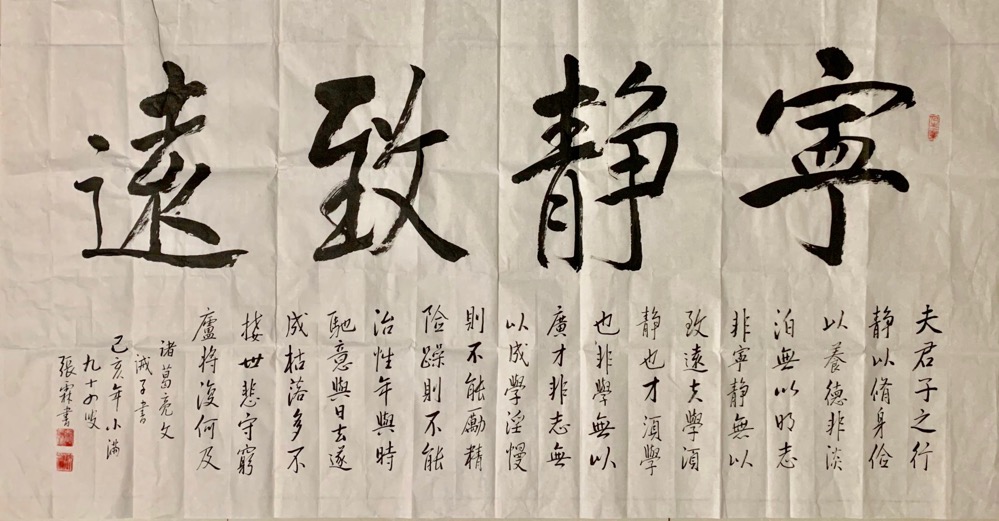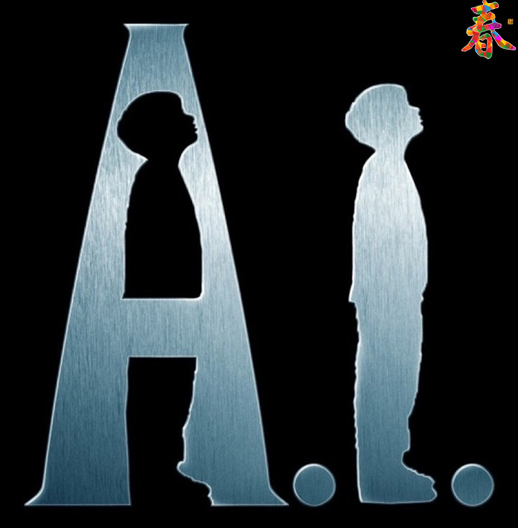我们关于技术的认识水平,大致相当于进化论出现之前的生物学。当时的生物学家确实对动物家族之间的关系了如指掌,但他们不了解进化论,他们不知道,所有这些动物,都是从哪里起源的。
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能如数家珍一般详细讨论某一种具体的技术对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的深远影响,但他们说不清楚技术的来源和进化。对技术最为熟悉的工程师们则对这一问题毫不感兴趣。
有一次,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问著名的技术专家沃尔特·文森蒂,为什么那么多绝顶的工程师,没有一个人尝试过建立一个关于技术的基础理论。文森蒂毫不迟疑地回答:“工程师们只喜欢那些他们能解决的问题。”
布莱恩·阿瑟决定自己动手,探索一个关于技术的基础理论。在《技术的本质》一书中,阿瑟声称,技术像生物一样,也是有基因、能突变,不断进化的。所有的技术,都脱胎于之前的技术,就像所有现存的生物,都能追根溯源地找到原始的祖先一样。
阿瑟试图找到各种千差万别的技术内在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解剖”技术,就会发现所有的技术都是一种组合。无论多么复杂的技术,都可以拆成若干模块,模块中又有零部件,这样不断地深挖下去,就会发现,复杂精妙的技术最终都是平凡的零部件的组合。
为什么技术要采取模块化的方式呢?
赫伯特·西蒙曾经讲过一个关于制表匠的寓言。假设每只手表都有1000个零件,第一个制表匠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安装,如果他出了一个小错,或是工作被打断,就得从头再来;第二个制表匠则把手表分为10个模块,每个模块中又有10个小模块,每个小模块中有10个零部件,那么,即使他装错了,或是工作被打断,损失的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
更重要的是,模块化的技术更适合进一步的创新:我们可以尝试把一个模块更新,或是对不同的模块进行新的组合。
那么,所有的这些技术,都是从哪里来的?
阿瑟提出,技术乃是对“现象”的捕捉。这听起来颇为异端,技术不是受科学的指导,是科学的应用版吗?
其实,科学和技术尽管联系紧密,但二者并非一体。直到20世纪初期以前,大部分技术发明都不需要科学的帮助。原始人看到剥落的燧石中,有尖锐的石片,可以方便地切割动物的肉和皮毛,就发明了石刀、石斧。热衷于炼金术和炼丹术的人们反复尝试,居然误打误撞地发现了很多化学技术。直到近期,技术发明才不得不大量从科学那里“借贷”,比如属于量子效应的核磁共振、隧道效应或受激效应,都是从科学理论中搬过来的。
即使是这些更加精密的技术,其本质也是对某种“现象”的捕捉和编码。技术人员和科学家不同,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应用。看到物体的摆动,他们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一“现象”做出时钟;了解到多普勒效应,他们会联系到可以利用这一“现象”测汽车超速。随着大量的“现象”被捕捉和编码,工程师们的工具箱里就更加琳琅满目。工程师们的工具箱里装满了他们已经学会的各种技术,这些技术构成了工程师们的“域”,也就是他们的活动范围。
大部分技术工作都是“日常标准工程”,即按照已经有的技术模版,不断“复制”出解决各种问题的新版本。无非是照章办事、比葫芦画瓢而已,最多是在应用于不同问题的时候,会有些小小的改动。但是,不要小看这些微小的变革,积少成多,这些不起眼的创新最后能导致巨大的变化。正如牛顿爵士所说的,顿悟来自于“连续不断的思考”。
当然,这不是否认重大的技术突破,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观察,重大的技术突破并非来自天才观点的横空出世。大部分技术的重大突破来自于对已有技术的重新组合,或是从其它的“域”里寻找新的工具。技术创新中应用的原理大多来自于已有的其它设备、方法,其它领域的理论,发明的核心就是“挪用”,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借鉴。
正如熊彼特所说的,创新就是新的组合。创新就是“混搭”,是把看起来没有联系的事物联系起来,以一种出其不意的组合重新展示给人们。所有的素材其实都在你的手边,而创新就是大胆地跨界、大胆地模仿:从来就没有什么新技术,也不靠专家院士。
当技术大潮到来的时候,不是经济适应技术,而是经济“遭遇”了技术。新一轮技术浪潮会让原有的生产模式土崩瓦解,社会组织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蒸汽机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纺织业,农户不再在家织作,而是到工厂里做工,成了工人。互联网时代又可能会再次颠覆工业革命以来的企业组织、用工制度,甚至教育体制。
技术永远都不完美,永远都在重构。技术是杂交的,不是纯种的;技术是峰回路转,不是金光大道;技术是随和迁就的,不是特立独行的;技术是有趣的,也是无聊的;技术既是残缺不全的,又是雷同冗杂的;技术吵吵闹闹,熙熙攘攘,凌乱无章,无视一切。
技术是一个复杂体系,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技术不是古板、冰冷的机械,而是生机勃勃的有机体。你侧耳倾听,才能听到它的婉转轻啼。